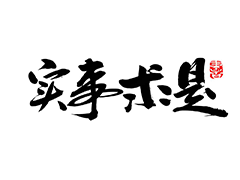在我国众多高等学府中,有这样一所大学,每年的三月份樱花盛开的季节,校园里便会上演一场粉、白色的视觉盛宴,将整个珞珈山装点得如诗如画,令人如痴如醉。
是的,它便是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樱花闻名遐迩,但除了美丽的樱花,武汉大学的背后,还有着一段段震撼人心、彰显铮铮铁骨的故事。
今天的文章,我就跟大家聊聊武汉大学的前世今生。
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正是在那一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创办了“自强学堂”,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之一。
“自强学堂”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以应对当时国家面临的危机。学堂开设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4门学科,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
1913年,“自强学堂”更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1924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又更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昌中山大学”与武汉地区的其他几所高校合并,正式成立“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学校开始在“珞珈山”建设新校区。
珞珈山校区是武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群,它将中西建筑风格完美融为一体,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珞珈山校区的建设,不仅为武汉大学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也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大学校园里风起云涌:师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致电当局,并游行请愿,表达他们的抗日诉求,开展国难演讲。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至1937年间,为了抗战宣传,“国立武汉大学”共举办国内演讲200多场。
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展捐献劳军活动,并收容大批战区转移来的学生,为抗战提供各种服务。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抱定“杀身成仁,尽忠报国”的信念和决心,组成“抗日铁血团”北上,走向抗战的最前沿。
他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敌机尚未飞走,就迅速组织救护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抢救工作中。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曾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直到1946年才迁回珞珈山。
即使环境极其艰难险恶,也没能摧垮武大师生的意志,武汉大学在战乱中依然名师云集,保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继续发展壮大。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的工科、农科、医科等学科被拆分到其他高校,但文理科依然保持在全国领先地位。
进入21世纪,武汉大学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武汉大学。这次合并,使武汉大学的学科门类更加齐全,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如今的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综合实力强劲的研究型大学,在各类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师生中展现出的无数令人敬佩的铮铮铁骨,就不能不让人想起王星拱。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曾经为武大注入灵魂的人物。
光绪十三年,王星拱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清贫书香人家,父亲王厚棋是清末秀才。
王星拱三岁时不幸丧母,五岁开始在外祖父的私塾中读书。他聪慧异常,又勤奋好学,经过私塾严格教育熏陶,8年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二十四史》等已了然于胸,因此深受外祖父母的钟爱。
1902年,14岁的王星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高等师范学堂,那是当时安徽省最高级学府。
1909年,21岁的王星拱告别家乡,远渡重洋来到比利时,先后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和根特大学,专攻化学和物理。
1916年,从英国伦敦大学硕士毕业后,王星拱结束了欧洲的求学生涯,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临行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学成归国,我当以所学报效祖国。
脚步还未踏上祖国的土地,王星拱就收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作为北大教授,王星拱在校内集会上发声,参与起草北大教授团声明,以实际行动公开积极支持爱国学生。
王星拱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立场,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政党。他认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应该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务。
尽管如此,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虽然王星拱没有直接参加会议,但他的一些建议被写入了党的纲领中。
除了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王星拱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北大期间发表了多篇重要的科学论文,涉及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等多个领域。
其中,他关于分子结构的一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现代化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由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突出贡献,1925年,王星拱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校长。
王星拱在武大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为武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
在长期的工作中,王星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主张,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设立农学院,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武汉成为战时陪都,面临着日军空袭的威胁。
在这危急时刻,王星拱做出了“带领全校师生西迁”的决定。他组织各系搬迁重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亲自带队徒步跋涉千里,最终在四川乐山安顿下来。
由于及时稳妥地做好了迁校准备,使武大在战时搬迁的诸大学中受损最小。
在乐山艰苦的条件下,王星拱依然坚持高质量的教学。他号召教师们“化艰难为力量,以困苦励学业”。
为了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他多次奔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拨款。同时,他还发动校友捐款,甚至变卖个人藏书来维持学校运转。
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占领了珞珈山校园,大肆破坏。得知这一消息,王星拱在日记中写道:“国难当头,吾辈更应奋发图强。他日光复武汉,定要将武大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西迁期间,王星拱并没有放弃学校的发展。他继续筹建新的学院,如农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学院不仅丰富了武汉大学的学科门类,还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医学院的建立,为战时医疗救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他还不顾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广揽学者名流。
他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往往亲自登门相邀,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取得了许多学术成就,使武大继30年代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后,再次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并誉为“四大名校”。
武大“乐山时期”的辉煌,王星拱当居首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星拱立即组织武汉大学师生回迁。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他带头清理废墟,修复校舍。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很快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并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
遭拒后,王星拱愤然辞职回乡。
1948年,王星拱辞任回到安庆。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屡次催逼他飞赴台湾,允诺予以重任,都被他毅然拒绝了。
1949年,王星拱在上海病逝,终年61岁。
当年,在上海的300多名武大校友不约而同赶去为他送行,陈毅市长亲手写了挽联,称王星拱为“一代完人”。
2008年,是武大西迁乐山70周年,也是王星拱诞辰120周年。
为了纪念这位为武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校长,武汉大学在武大校园里,为王星拱修建了一座雕像。
王星拱的一生,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半个世纪。这位老校长,用他17年的呕心沥血,为武汉大学、为新中国培养出了无数铮铮铁骨和国之栋梁。
今年的樱花季已经过去了,不知道,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武汉大学的校园,是否还能像往年那般芳香四溢。不知道他们九泉之下的那位老校长,是否还会像从前那样,感到骄傲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