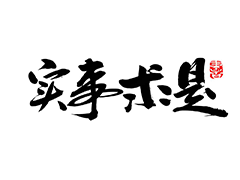文/猫眼
一池显影液泛起血色的涟漪,模糊的影像在红光中逐渐清晰,而历史在暗房里苏醒。—《南京照相馆》
当婴儿的啼哭声划破了虚假的“亲善”拍摄现场,下一秒幼小的身躯被日军士兵拎起砸向青石板。
随后那声戛然而止的啼哭与母亲撕心裂肺的哀嚎交织,而影院里的抽泣声也如潮水般蔓延……
截止到10号,上映17天的《南京照相馆》已破20亿,预估42亿,可以说一举打破了暑期档的平淡高歌猛进,片子的大火再一次证明了好的作品一定不愁卖座。
申奥导演以1937年南京沦陷时期的“吉祥照相馆”为舞台,将邮差阿昌、照相馆老板老金、女演员林毓秀、翻译官王广海这几个普通人在至暗时刻推入历史漩涡的中心。
他们被迫为日军冲洗照片,意外发现了记录暴行的底片,由此踏上了冒死传递真相的荆棘之路。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保卫战中,照相馆的暗房成了历史的审判台,显影液成了洗刷谎言的圣水。
当显影液中的影像逐渐在《南京照相馆》的暗房红光中浮现,银幕前的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张张底片的显影,更是一个民族被遮蔽的记忆在艺术中的艰难复苏。
整部作品来看并非单靠情感价值卖的座,而是在影视美学影视艺术上也非常值得票价。
比如克制和留白的艺术美学,在历史惨剧的影像呈现上,《南京照相馆》以克制代替了渲染,以留白填补了血腥。
影片对暴力的呈现堪称“优雅的残酷”,很多暴行并非通过直观画面冲击观众,而是通过母亲瞬间崩溃的面部特写、翻译官颤抖的双手、以及被迫拍摄“全家福”时那扭曲的假笑,还有女主脸上的伤痕凌乱的衣物等等暗示。
这种留白与克制的处理反而能在观众想象中投射出更广阔的恐怖空间,比任何直白画面更能传递战争对人性摧残的本质。
而在视觉与隐喻上,作品用整个暗房场景的象征体系构建了影片的精神核心。
红光弥漫的密闭空间如同母体,孕育着即将诞生的历史真相,显影液中翻滚的影像宛如血浪,与日军擦拭军刀的画面交叉剪辑,揭露暴力与伪善的一体两面。
老金的一滴泪坠入药水的特写镜头,将个人悲痛溶解进民族苦难的长河,这些影像不单是技术操作过程的记录,更成为历史记忆修复的仪式性场景。
而日军摄影师按下快门的声音与枪械上膛声通过蒙太奇剪辑重叠时,一种残酷的隐喻诞生了:
影像权即话语权,相机与枪炮同样致命。
看到这希望各位看官,记住这句话后面要考。
接着说在细节处《南京照相馆》编织了一张精密的符号网络,每个细节都承载着历史的密码。
比如数字与姓名的隐喻,邮差苏柳昌的编号“1213”与照相馆门牌“1937”组合成南京沦陷日“1937年12月13日”,而角色的姓名“苏柳昌、金承宗、林毓秀”谐音“江苏金陵”。
还有影片中宋存义砸向日军的城墙砖,砖面刻有明代工匠姓名,直指日军掠夺南京城砖建造“八纮一宇塔”的史实。
从人物塑造上《南京照相馆》从真实小人物出发拒绝塑造非黑即白的英雄,很诚恳的将镜头深入到了人性的灰色地带,细致的去描写人性一点点的变化。
比如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从瑟缩偷生、私藏干粮的利己主义者,蜕变为用身体护住底片的真相守护者,作品用三次冲洗关键底片的递进设计,见证了其精神觉醒的合理轨迹。
而王传君饰演的翻译官王广海,其谄媚求生的表象下藏着良知的暗流,这个投机主义者的良知从他目睹婴儿被摔时别过的脸,交出通行证时滚动的喉结都有预示,从为了生存苟活到确认真相后的醒悟,整个过程都设计的很好……
同样其他的角色整部剧也安排的非常好很细腻很真实,而更为艺术的是这部影片的声音设计给观众构建了独特的战争听觉记忆。
比如当童谣与欢呼的残酷交响声对比,当南京的童谣《城门几丈高》与日军的欢呼声重叠到一起时,那种文化与听觉产生的撕裂让人极度窒息。
此外还有机械声响的死亡隐喻,剧中的相机换胶卷声似子弹上膛,暗房定时器的滴答如生命倒计时。
比如老金中弹时用相机破碎声替代枪响,再一次郑重的说明影像权即话语权,话语权即生命权。
因此,综上所述这部电影作品无论是从情感传递还是本身影视美学亦或者演员演技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优质作品。
面对着这样一个将历史真实记录用优质的视听美学演绎出来的作品,可以因为内心的难受和痛苦而不敢看不去看,但是要用其他角度来污蔑和抹黑,就真的得好好聊一聊了。
比如最近冒出不少人用刁钻的角度来抨击这部作品煽动仇恨和民C。
他们拿着那被西方媒体美誉成世界上“最伟大最反战”的“人道主义”作品的《辛德勒名单》来背书,对前者极尽诋毁,对后者却极尽赞美和夸耀。
就仿佛他们也是西方人的一份子,站在局外用着“圣母”的眼光自认为“悲悯”的发出着令人刺耳的——犬吠声。
郭德纲说过如果有人在你被人“两肋插刀”后,不去谴责插刀者而是一直告诫你要宽容要大度要善良,要么给他一下子要么离他远点,站着说话的永远不腰疼。
《辛特勒名单》原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影视剧导演是美国人斯皮尔伯格。
一个澳大利亚和一个美国人创作的讲述德国二战的故事,他们当然可以冷静可以理智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想象去美化他国战争里的人性。
这些西方人打造出“圣母悲悯劝架老好人”的形象塑造着那伪善的虚假的世人面具,他们和《南京照相馆》中那些拿着相机和糖给孩子拍照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禁要问那高喊着要让《南京照相馆》学习《辛特勒名单》的人,你们也是这般伪善的站在旁观者角度的第三方么?
德国忏悔了道歉了认错了甚至下跪了,日本道歉了?认错了?正视历史了?
加害者还没道歉还在篡改历史,你们这些受害者就想着遗忘想着忘却想着抹黑,明明是受害者后裔却要数典忘祖,你们可配人子?
《辛德勒名单》一个国外屡次获奖的大片,不少人被他的善举感动的稀里哗啦,真实历史的犹太人感动了么?
事实是历史上的辛德勒最后穷困潦倒时犹太人并没有给他帮助,事实是犹太人在对巴人民进行更残酷的伤害。
真实的辛德勒本身就有着复杂的身份,他初期是绝对的剥削者,更是纳粹军官,本人有着极强的投机主义,而这些却在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作品美化中被淡化的微乎其微,他们把辛德勒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救世主,像每一个西方人编织的每一个谎言一样。
斯皮尔伯格镜头下的辛德勒,是一个被精心提纯的“人性救世主”。
电影刻意淡化其作为纳粹间谍、投机商人、道德瑕疵者的复杂底色,转而将红衣小女孩的意象作为其“人性觉醒”的开关,完成从剥削者到拯救者的嬗变
历史的真相是辛德勒初期雇佣犹太人仅因他们是“近乎免费的劳动力”,其工厂利润直接源于纳粹的种族压迫体系。
他是以德国军事反间谍组织策划的身份入侵的波兰,而影片也将这一背景剥离,使其纳粹党员身份仅沦为情节工具。
至于个人德行辛德勒就更是一塌糊涂堪称烂人,然而相机和媒体就是有把一个啥也不是的人美化成为“高光圣父”的能力,而这也是西方人掌握话权后一贯的做法。
《辛德勒名单》在巴以冲突后分数骤降,因为用现实说话后,他们用镜头编织的伪童话被世界彻底看穿,一切全都是伪善者的自我美化,围观别人的悲惨时高喊着宽容善良与大度,一轮到自己那真是满嘴的獠牙狰狞可怖。
而且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本身就有着“五十万买卖面包”的复杂剥削渊源,而我们可卖给过日本人五十万一块的面包?
一个二战时没有侵略、欺负和剥削过任何他人的国家,其人民却被残忍屠戮与,之后加害者还不断的篡改历史扭曲事实,然而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只是想铭记历史,希望被世界看到被隐瞒的真实的历史真相,有人却来劝我们放下,而这些人还是所谓的自己人。
借用吴师傅一句话:这些人你们见不见呐?
满嘴的文明满嘴的仁义道德,其实内里全是男盗女……
那些对西方向往,那些不顾事实就满足于西方编织的童话世界的人,不知道是真幼稚的可怜,还是内心其实有着自己的小九九?请自己摸着良心来回答,如果有的话。
最后目前看来无论《辛德勒名单》获了多少奖有多少美誉,只要美国没有停下自己到处纵火的心,它就是一部带着伪善面具的胡诌作品。
现在看起来影片中那些拿着相机和糖的日本人不就像极了打着悲悯旗号拍摄《辛德勒名单》的美国人斯皮尔伯格?
至于那些西式思考的人,好好看看自己,你们不是美国人不是澳大利亚人,你们是牺牲了千百万前辈性命才留下的生命延续体,所以可否好好做个……人?举报/反馈